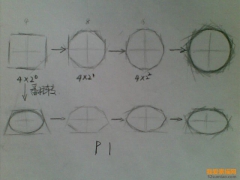要“意”不要“真”,要“似”不要“全”。
張大千先生1957年在法國會見了畢加索大師,畢加素對張先生說:“我最不懂的是你們中國人,為什么跑到巴黎來學藝術”?他又說:“在這個世界上要談藝 術,第一個是中國人的藝術,整個西方、白人都沒有藝術”!他的話有些過激,但絕非聳人聽聞,中國有著五千年文化藝術積淀,藝術成就博大精深,可我們自己的 發掘和研究遠遠不夠。這一寶庫有待后人去繼續完成挖掘開發!
徐悲鴻先生的油畫《簫聲》(1926)就是洋為中用的最完美的中國油畫的典范。董希文先生畫的“開國大典”同樣是這一結合的極為優秀的作品。
我們中國的傳統音樂、戲劇、美術,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是旨在表現,中國的藝術學派總體上是一個表現的藝術體系,在世界上早已被世人矚目。
李可染先生說:“要以最大的功力打進去,還要以最大的勇氣打出來”!對西方的素描藝術只要肯學,打進去并不難,而要打出來,光憑勇氣還不夠,必須認真學習 和繼承傳統,否則會越學越洋,萬變不離洋人的條條框框。在這方面要學林楓眠先生,他不東拼西湊,他的畫有中國氣派。學西方不一定要徹底地學,學得越像西方 越難走出來,越沒出息。
俄羅斯美術教育家契斯恰柯夫所主張的“體面要無休止地分割下去”的理論是正確的,有科學性的,但它純屬自然屬性的東西,非藝術追求。在畫面上無休止地分析體面對藝術表現有多大用處?在藝術表現這個大課題中,不應把精力投向這些非主要方面。
在空間處理上,素描要求每個地方都要畫到位,要在每個空間位置上呆得住,花力氣是可做到的,但它還離不開“真”與“像”的范疇,皆為自然屬性,而非藝術語 言。一切嚴格的規律性與科學性的要求可以做到,但過了頭就會成為藝術創造的框框,成為追求情、意、神、韻的“緊箍咒”。
“洋為中用”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上吸收泊來之精華,不是代替我們的傳統,這是個認識問題。只知西方素描,只接受西方藝術觀念,想的是洋人走過的路,洋人的一切都要陳陳相因,還談什么洋為中用?那只會從洋到洋,洋到底。
羅工柳先生早在20世紀三十年代就在杭州藝專學習西方素描,五十年代又去俄羅斯進修油畫。可是他從不放棄對中國傳統書法、中國古代壁畫、民間藝術、古代文 物的精深研究與鐘愛。他沒有被西方藝術引入洋化之路,從寫實到寫意,把情與意當作主宰,追求變化于有中國氣派的新與奇,怪與絕。
中國和西方藝術傳統在觀念上截然不同,拿來主義不可取,拿來之后要用中國文化傳統作為消化液,去消化它;沒有這種消化液必被全盤西化,在虛偽的“世界化”的幌子之下被西化。必須要中國化!
年輕的畫家與學子,必須補上學習和繼承中國文化傳統這一課,要學中國的書法藝術,中國的音樂與戲劇和幾千年的優秀遺產。“洋化”是死路一條。
藝術的發展要求“異”而不是“同”。“異”首先是和西方藝術唱反調,在素描常規要求中去加強對表現的研究,強調中國的民族精神、民族特點,追求開朗明快、健康向上、大度豪氣的中國氣魄!
·不要白開水·
“氣韻生動”六法之首,中國藝術歷來推崇比真實更高的表現主義。重情感之表達,抒內功之氣,求韻味品律,揚磅礴之氣,求真而不追實。把生活之氣息、語言之喻情,色彩之強烈,造型之夸張融入作品之中,使其具有震撼力為追求的最高目標,構成中國的藝術之魂。
李白酒醉而吟詩,石濤推杯而舞墨,都是在強烈的刺激之下,抒發胸中之氣。阿炳一把二胡拉出了千古絕唱《二泉映月》。錢紹武先生熟讀古書,博覽中國古代石 窟,創作出獨具中國氣派與風格的“李大釗像”。羅工柳先生身患絕癥,以對疾病的大無畏藐視,寫出了一幅幅狂草,大氣獨韻,似酒后忘情之狂舞。他創作的一幅 幅抒寫大氣之勢的油畫,意氣風發,如有神助。
京劇名家們,每唱一句都會引發臺下雷鳴般掌聲,喝彩聲聲不斷,為什么?韻之美、聲之美、味之美、腔之美,繞梁三日回味無窮。
中國當代繪畫在不久的將來,定會在世界上博得喝采,博得尊重。我們不能不看到,中國現今造型藝術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由教師和學子們的高度敬業、勤奮、苦練 于朝暮之間所獲得的扎實基本功而成。是多少教師風雨無阻披星戴月不計報酬的全心全意地教學,是學生輩不分寒暑一心一意地苦練的結果。這與在商品經濟沖擊下 的那些急功近利之作,比那些缺乏師德,不負責任,誤人子弟之流形成鮮明對比。